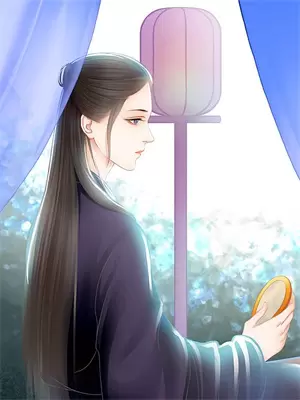1沈安安裹紧了身上略显单薄的外套,
N次确认了背包里的装备:高强度手电筒、红外线测温仪、运动相机、还有一大包……零食。
没错,零食。毕竟,漫长的夜晚需要热量来对抗恐惧,哪怕这恐惧可能来自非科学领域。她,
沈安安,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自由职业者,目前的主业是——凶宅试睡员。听起来很酷?
实际上就是在各种传说闹鬼、死过人的房子里住上几晚,写份体验报告,
安抚潜在买家或租客脆弱的心灵,顺便赚点辛苦费。
眼前这栋苏家老宅后院的独立小院——“静园”,就是她最新的“工作地点”。资料上说,
这里几十年前曾有一位苏家小姐投井自尽,此后便怪事不断,
夜半哭声、井口异响、物件莫名移动……总之,
是苏家急于出手但又碍于面子不好明说的“瑕疵资产”。报酬相当丰厚,
抵得上她平常接三四单。虽然苏家联系人,那位姓莫的婆婆,眼神古怪,
叮嘱的规矩也多比如入夜后绝不能去后院古井附近,但看在钱的份上,
沈安安还是硬着头皮接下了。
“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……”她一边小声念叨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自己壮胆,
一边推开了静园主屋那扇沉重的、带着陈旧雕花的木门。
吱呀——一股混合着霉味和淡淡灰尘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屋子很大,家具都是深色的老物件,
在黄昏晦暗的光线下显得影影绰绰。空气里,
似乎还飘荡着一丝若有若无的、清冷的香料气息。“啧,这氛围感,直接拉满。
”沈安安吐槽一句,打开手电,开始布置设备。她没注意到,在她踏入静园的瞬间,
后院那口被石板半掩的古井井沿上,几滴冰冷的水珠,无声无息地渗了出来,缓缓滑落。
入夜,万籁俱寂。沈安安啃着薯片,盯着相机显示屏和测温仪数据。
一切正常……正常得有点过分。除了温度似乎比外面低了几度,
以及那若有若无的香料味似乎更浓了些。“就这?看来又是以讹传讹。”她打了个哈欠,
准备收工睡觉。这单钱赚得似乎比想象中容易。就在这时——“咚。
”一声极其轻微的、像是手指关节敲击实木的声音,清晰地从房间某个角落传来。
沈安安瞬间僵住,薯片袋掉在地上。不是错觉!她猛地抓起手电筒扫过去,光线所及,
只有沉默的家具和墙壁上的阴影。“谁?谁在那里?”她的声音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。
无人回应。但下一秒,放在梳妆台上的红外线测温仪,屏幕上的数字开始疯狂跳动,
从18℃一路暴跌至5℃!同时,那清冷的香料气息骤然变得浓郁,几乎充斥了整个房间!
沈安安寒毛倒竖,心脏狂跳!她看到梳妆台那面模糊的铜镜里,自己的影像似乎扭曲了一下,
肩膀后面,好像……多了一团模糊的白影?
“阿弥陀佛上帝保佑真主安拉……”她语无伦次地开始念诵所有能想到的神佛之名,
手脚发软地往门口退。然而,房门像是被焊死了一样,纹丝不动!“咚!咚!咚!
”敲击声再次响起,这次变得急促、有力,仿佛带着某种不耐烦的情绪,来自……床的方向?
沈安安惊恐地望去,房间中央那张仿古的拔步床,暗红色的帐幔无风自动,微微摇晃起来。
帐幔之后,似乎有一个极其高大的、模糊的黑色人影轮廓,缓缓坐起!
冰冷的、如同实质的视线,牢牢锁定了她!完蛋!真撞邪了!还是个大个的!
沈安安脑子里一片空白,只剩下本能驱使着她,转身就想从窗户逃走。
可窗户也不知何时被从外面封死!“救……救命啊!”她带着哭腔喊道,徒劳地拍打着门窗。
就在她绝望之际,一个冰冷、低沉、带着无尽威严与漠然的声音,
直接在她脑海中响起:“聒噪。”沈安安的哭喊戛然而止,吓得打了个嗝。那声音继续道,
不带丝毫感情:“闯入吾之沉眠之地,扰吾清净……按契约为奴为婢,或,死。”契、契约?
为奴为婢?这都什么跟什么?!沈安安欲哭无泪,试图讲道理:“大、大哥……不对,
鬼王大人?我就是个临时工,来试睡的,不知道这是您的地盘啊!我这就走,马上走,
保证再也不来了行不行?”“契约已启,由不得你。”冰冷的声音打断她,“要么,
签下魂契,暂代‘新娘’之位,安抚此地躁动怨气,助吾稳固神魂。事成之后,
或可放你离去。”“要么……”帐幔后的黑影似乎动了一下,房间内的温度瞬间降至冰点,
“现在便成为它们的一部分。”它们?沈安安这才惊恐地发现,房间的阴影里,
似乎有更多模糊扭曲的身影在蠕动,散发着浓郁的恶意!新娘?!和个鬼王联姻?!
这比为奴为婢还离谱!“我、我选C行不行?”沈安安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挣扎。“死。
”冰冷的宣判毫无转圜余地。看着周围越来越近的阴影,感受着那几乎冻结灵魂的寒意,
沈安安把心一横,牙一咬:“我签!我签还不行吗!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!
先保住小命再说!“识时务。”冰冷的声音似乎闪过一丝几不可察的……满意?
一道散发着幽光的、由诡异符文构成的卷轴,凭空出现在沈安安面前。
她甚至没看清上面写了什么,只觉得指尖一痛,一滴血珠飞出,融入了卷轴。卷轴化作流光,
消散在空中。 同时,她感觉手腕一凉,一道淡淡的、像是绳索勒过的红痕浮现出来。
周围的阴影发出不甘的嘶鸣,缓缓退去。房间的温度也开始回升。帐幔后的黑影重新躺下,
恢复了寂静,只留下最后一句话在她脑海回荡:“明日,苏家会有人来接你。
扮演好你的‘角色’……”沈安安虚脱般地滑坐在地上,看着手腕上那道诡异的红痕,
欲哭无泪。救命!凶宅试睡不仅撞邪了,还被个鬼王强行联姻了!这找谁说理去?!
她这算不算……工伤?2第二天,天刚蒙蒙亮,静园外就传来了脚步声。
沈安安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,一夜未眠。
手腕上那道冰冷的红痕时刻提醒着她昨晚匪夷所思的遭遇不是梦。门被从外面打开,
出现的正是之前联系她的莫婆婆。她穿着一身古怪的深色长袍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
浑浊的眼睛在沈安安脸上和手腕的红痕上扫过,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精光。“沈小姐,
休息得可好?”莫婆婆的声音干涩沙哑。沈安安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:“……挺好。
”好到差点和鬼王成了亲!莫婆婆似乎并不在意她的回答,只是淡淡道:“既然醒了,
就跟我走吧。夫人要见你。”“夫人?哪个夫人?”沈安安一愣。“苏夫人,苏家的主母。
”莫婆婆转身带路,“你既是静园选中的‘有缘人’,有些规矩,夫人要亲自交代。
”有缘人?沈安安嘴角抽搐,是被鬼王强行绑定的倒霉蛋才对吧!她跟着莫婆婆走出静园,
穿过曲折的回廊,走向苏家老宅的主楼。一路上,遇到的佣人都低着头,脚步匆匆,
没人敢多看她们一眼,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水珠一下一下,砸在锃亮的黄铜洗手盆里。
咚。咚。在苏家老宅那过分奢华也过分安静的洗手间里,沈安安掬起一捧冷水拍在脸上,
试图驱散那股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和寒意。镜子里的人,脸色苍白,
眼下带着浓重的青黑。她被带到这里,换上了一身极为昂贵的定制中式礼服,
金线绣出的鸾凤和鸣图案,在顶灯下流转着过于精致的光泽。但这身价值不菲的行头,
并没给她带来丝毫暖意,反而像一层冰冷的壳。莫婆婆告诉她,
今天是苏家小少爷苏黎的“冲喜”之日,而她,就是被选中的“新娘”。沈安安当时就懵了。
冲喜?这都什么年代了?而且苏家小少爷不是据说病得只剩一口气,是个植物人吗?
让她一个陌生人去冲喜?联想到昨晚鬼王说的“扮演好角色”以及苏家对静园的态度,
一个荒谬又恐怖的猜想在她脑中形成——苏家知道静园里有“东西”,他们所谓的冲喜,
很可能与鬼王有关!他们想利用她这个被鬼王“标记”的人,达到某种目的!“沈小姐,
准备好了吗?夫人和仪式都在等了。”门外传来莫婆婆催促的声音。沈安安深吸一口气,
推开沉重的洗手间门。走廊铺着厚厚的地毯,脚步声被完全吸收。
两个穿着黑色西装、耳廓上挂着透明通讯线的保镖,像两尊没有生命的雕塑,
静默地站在一间病房门外。看到她过来,其中一人无声地推开了房门。
病房里更是安静得可怕。消毒水味混合着那种清冷的香料气息。窗帘紧闭,
只有角落一盏落地灯散发着幽暗的光,照亮房间中央那张巨大的医疗床。床上,
躺着一个闭着眼的年轻男子。苏黎。他脸色是一种近乎透明的苍白,长得极好,但了无生气。
床边,站着苏夫人,莫婆婆,还有两个神情严肃的医生。“开始吧。”苏夫人看向沈安安,
声音很轻,却带着不容置疑。莫婆婆走上前,手里端着木质托盘,上面是两只白玉酒杯,
盛着暗红色的液体,散发出药味和一丝极淡的腥气。沈安安的心沉到了谷底。这仪式,
果然不对劲!她被迫喝下那杯味道古怪的“酒”,一股灼热感滑下,
随即化作奇异的暖流涌向四肢,带来轻微的眩晕。接着,莫婆婆用一红一黑两股细绳,
将她的左手手腕和苏黎的右手手腕紧紧捆在了一起。绳子触感冰凉滑腻,绑上的瞬间,
沈安安莫名地打了个寒颤。“阴阳相牵,气血相连……”莫婆婆开始念念有词。
沈安安僵硬地站在床边,靠近那张苍白的脸。离得近了,她能看清他皮肤下淡青色的血管。
仪式在继续。莫婆婆的声音忽高忽低。房间里的灯似乎暗了一下。
沈安安觉得那股眩晕感在加重,身体里的暖流变得躁动,带着刺痛。她开始害怕,
想挣脱绳子,却发现莫婆婆枯瘦的手指蕴含着意想不到的力量。
就在莫婆婆的吟诵声陡然拔高,变得尖利刺耳的那一刻——“啪!”整个房间,
瞬间陷入一片纯粹的、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!所有仪器运作的声音,戛然而止!停电了!
“啊!”沈安安短促地惊叫。黑暗中,一片死寂和混乱。就在这片极致的黑暗和混乱中。
沈安安猛地感觉到,那只一直被绳子绑着、冰冷僵硬的、属于苏黎的手,动了一下!
不是无意识的抽搐。是翻转!然后,一只冰冷彻骨、僵硬得如同铁钳般的手,
猛地、死死地攥住了她的手腕!那力度极大,捏得她腕骨生疼!“啊——!!!”这一次,
是真正凄厉的尖叫。几乎在同一时间,应急灯“嗡”地一声亮起,投下惨白的光晕。
光线回来的瞬间,沈安安的瞳孔骤然收缩。病床上,
那个被宣告为植物人的苏黎……竟然……直挺挺地……坐了起来!他的眼睛,依旧紧闭着。
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但那坐起的姿势,僵硬得如同提线木偶。而那只冰冷的手,
正以一种绝对占有的、不容挣脱的姿态,紧紧箍在沈安安纤细的手腕上,
红黑两色的绳子深陷进皮肉里。“呃……”一个医生吓得倒退一步。苏夫人也惊呆了。死寂。
几秒钟后。“砰!”病房门被撞开,一个保镖连滚爬爬地冲进来,
脸上是全无血色的惊恐:“夫…夫人!
监…监控室刚…刚才短暂恢复了一瞬……拍…拍到了……”另一个医生像是猛地反应过来,
扑到监护仪前,手忙脚乱地操作,随即颤抖地触碰到苏黎颈侧动脉。下一秒,
他发出扭曲的尖叫,连滚爬爬地逃离床边,指着那直挺挺坐着的“人”,
眼珠几乎瞪出来:“不对!不对!他不是植物人!他……他早就脑死亡了!
至少……至少超过48小时了!!这不可能!!”脑死亡超过两天的人……坐了起来,
紧紧抓住了她的手腕。沈安安看着眼前这超乎理解的一幕,感受着手腕上那冰冷刺骨的抓握,
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在疯狂叫嚣:救命!这根本不是冲喜!3她好像……摊上大事了!
手腕上那圈青紫的淤痕火辣辣地疼,像一道冰冷的烙印,
时刻提醒着沈安安病房里那匪夷所思的一幕——脑死亡超过四十八小时的苏黎,
直挺挺地坐起来,用一只冰冷僵硬的手,死死抓住了她。她被半强制地送回了静园,
与那个“苏醒”后又恢复沉寂的苏黎一起。静园的门窗被加固,看守更加严密,
她彻底成了一只被困在金丝笼里的雀鸟,只不过这只笼子弥漫着陈腐的香气和无声的恐怖。
苏黎被重新安置在那张巨大的拔步床上,暗红色的帐幔再次低垂,隔绝了内外。
他大部分时间如同真正的植物人般安静,但沈安安能感觉到,
那道冰冷的意识始终萦绕在房间里,如同潜伏在深海下的巨兽,无声地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。
偶尔,在深夜,她会听到帐幔后传来极其轻微的、像是骨骼摩擦的“咯吱”声,
或是感觉到一道冰冷的视线穿透帐幔,落在她的背上,让她汗毛倒竖。
苏夫人和莫婆婆来过几次。苏夫人看她的眼神复杂难辨,有审视,有估量,
甚至还有一丝隐藏极深的忌惮,仿佛她不再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孤女,
而是某种不可控的变数。莫婆婆则更关心她手腕上那道淤痕和她的精神状态,
反复叮嘱她要“安心陪伴”,并更换了床头安神香的种类,那香气愈发浓郁甜腻,
几乎让人窒息。他们绝口不提医院里发生的异状,仿佛那只是一场集体幻觉。但沈安安知道,
那不是幻觉。苏黎体内的“东西”是真实存在的,而苏家,显然知情,
并且仍在继续他们的计划。绝望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她,越收越紧。她不能坐以待毙,
成为这场诡异仪式的最终祭品。转机,在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悄然来临。狂风呼啸,
雨点密集地砸在屋顶和窗棂上,发出巨大的噪音,反而掩盖了静园内许多细微的声响。
也许是天气扰乱了某种无形的屏障,也许是那“东西”的注意力被分散,
一直萦绕在沈安安心头的冰冷压迫感,似乎减弱了些许。就在她蜷缩在软榻上,
听着窗外雨声昏昏欲睡时,一阵极其微弱、断断续续的啜泣声,再次飘入了她的耳中。
这一次,声音不再飘忽不定,而是隐隐指向一个方向——后院。是那个民国少女的残魂!
苏婉清!沈安安的心脏猛地一跳。她想起之前镜中的影像和那若有若无的求助。这是个机会!
她屏住呼吸,悄悄爬到窗边,透过被雨水模糊的玻璃,望向漆黑一片的后院。
那口被石板半掩的古井,在雨幕中如同一个蛰伏的怪兽。“是……你吗?”她鼓起勇气,
用极低的声音,对着窗外雨幕的方向问道,“苏婉清?”啜泣声戛然而止。几秒后,
一段更加清晰、却充满悲伤与焦急的意识流,强行挤入了沈安安的脑海,
成最后的‘融灵’……”“井……井下……有秘密……有……阻止他的……线索……”融灵?
沈安安心中骇然。果然是要用她的灵魂或者生命,去填补或者唤醒苏黎体内的那个怪物吗?
“什么线索?我该怎么帮你?”她急忙在心中追问。
“玉……我的……玉佩……被他们……扔在井里……”苏婉清的意识断断续续,
仿佛维持这种沟通极为费力,
……”“井底……不止有我……还有……苏家……真正的……罪孽……守印人……”守印人?
罪孽?信息到此骤然中断!一股强横冰冷的意识如同寒风般扫过整个静园,
带着被打扰的愠怒。是苏黎或者说他体内的存在!拔步床的方向,帐幔无风自动,
剧烈地晃动了一下,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躁动不安。沈安安吓得立刻噤声,缩回软榻,
心脏狂跳。那冰冷的意识在房间里盘旋片刻,似乎在搜寻着什么,最终缓缓退去,
重新归于沉寂。但那种被顶级掠食者盯上的恐惧感,久久不散。后半夜,沈安安再无睡意。
4那口古井,不仅是苏婉清的葬身之地,更是解开所有谜团的关键!可是,
她该如何突破严密的看守,去到那口被明确禁止靠近的古井?就算到了井边,
她又该如何下到井底?井下等待她的,除了线索,会不会还有更恐怖的东西?
雨水敲打窗棂的声音渐渐稀疏,天边泛起一丝微弱的灰白。
沈安安望着窗外逐渐清晰的、荒草丛生的后院,目光最终落在那口沉默的古井上。
恐惧依然存在,但一股破釜沉舟的勇气,也在她心底慢慢滋生。她必须找到机会,
去井下一探究竟。这是她唯一的生路。她必须找到那块玉!
机会来自负责送饭的怯懦女佣阿香。在一次送饭时,阿香趁无人注意,
飞快地塞给沈安安一个油布包,眼神惊恐却坚定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