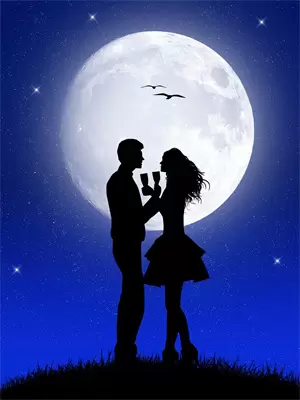1 被遗忘的尊严被时代碾过的人:老陈那是我在城郊结合部出租屋里见过的邻居,老陈。
记忆里,他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工装,脊背佝偻得像一张拉满的弓,
走路时左脚拖着地,发出“沙沙”的摩擦声。他那张脸布满沟壑,眼窝深陷,
看人时目光总是怯怯的,仿佛随时准备挨骂。老陈住在我们那栋筒子楼最尽头的一间小屋,
不到十平米,月租三百。我搬进去的第一天,就因为扔一个纸箱而认识了他。
“这个……您不要了?”他站在垃圾桶旁,手指小心翼翼地触碰那个我刚丢的快递纸箱。
“不要了,你拿去吧。”他像得了什么恩赐,连连鞠躬:“谢谢,谢谢您!
”后来我从房东那里得知,老陈靠捡废品为生,是这栋楼里住得最久、也最穷的租户。
“也是个可怜人,”房东撇撇嘴,“以前还是国营厂的工程师呢,后来下岗了,
老婆跟人跑了,儿子也死了,人就垮了。”2 荣光与坠落曾经的荣光某个周末,
我因为工作调休在家,老陈敲门送来一个他捡到却修好的小台灯,我请他进来喝杯茶。
几杯廉价的茉莉花茶下肚,他终于慢慢打开了话匣子。“1985年,我是厂里的技术标兵,
”老陈的眼睛突然有了光彩,“那时候在红星机械厂,谁不知道我陈国栋的名字?
我设计的模具,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!”他从一个铁皮盒子里拿出几张发黄的照片。
照片上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,站在一台庞大的机器旁,胸前戴着大红花,
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。我很难把照片上的青年和眼前这个佝偻的老人联系起来。“那时候,
厂里分配了住房,两室一厅,亮堂得很。我媳妇是经人介绍的,小学老师,人长得秀气,
儿子虎头虎脑,成绩也好。”老陈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,
“谁能想到呢……”3 命运的转折坠落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
那场席卷全国的国企改革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,老陈是其中之一。“厂子先是说效益不好,
减薪,后来干脆宣布破产。”老陈盯着手中那杯浑浊的茶水,“我们三百多号人,
一夜之间全下岗了。”四十多岁,身怀一门看似过时的技术,
老陈突然发现自己在这个飞速变化的社会里毫无用处。他去建筑工地搬过砖,摆过地摊,
甚至蹬过三轮,但总是做不长久。“媳妇开始还安慰我,后来就总是抱怨。有一天我回家,
发现她带着儿子走了,只留下一张字条,说‘这日子过不下去了’。”老陈找过他们很多次,
最终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前妻和儿子。她已经重组了家庭,嫁给了一个小生意人。
“我儿子看见我,眼神躲躲闪闪的,叫了声‘陈叔叔’就走了。”老陈说这话时,
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。4 最后根稻草最后一根稻草下岗后的第五年,
老陈勉强在一个私人小作坊找到了工作,虽然工资不高,但总算能糊口。就在这时,
他接到了前妻的电话——他们的儿子被查出白血病,需要巨额医疗费。
老陈变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,向所有还能联系的亲友借钱,凑了八万块钱送去。“那段时间,
我白天在作坊干活,晚上去车站扛包,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。”老陈说,
“但只要想到能救我儿子的命,累也值得。”然而,命运并没有眷顾这个已经跌入谷底的人。
半年后,儿子还是走了。葬礼上,前妻哭喊着捶打他:“都是跟你过的苦日子害的!
要是他生在个好人家,怎么会得这病!”这句话像一把钝刀,
彻底割断了老陈与这个世界最后的温情联系。儿子去世后,老陈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。
他无法集中精力工作,最终被作坊辞退。没有了收入,他租不起原来的房子,
只好搬到这个城郊结合部的筒子楼里。5 帮助的困境为什么没有人帮助他?这个问题,
在我了解老陈的故事后,曾反复思考。事实上,有人曾试图帮助过他。他刚下岗时,
原来的老同事凑钱借给他,
过最初的日子;街道办事处曾给他介绍过保安的工作;甚至他的亲戚也曾接纳过他暂住家中。
但为什么这些帮助最终都没有改变他的命运?第一,尊严的代价老陈曾提到,
他去申请低保时,工作人员那公事公办的态度和偶尔流露的不耐烦,
让他觉得自己是个社会的累赘。“他们让我填无数表格,在不同办公室之间跑来跑去,
最后告诉我材料不全。”老陈回忆道,“我站在那个大厅里,感觉所有人都在看我,
看我这个没用的下岗工人。”这种尊严的损耗,对曾经是技术标兵的老陈来说,
是难以承受的。他宁愿捡废品,也不愿再面对那种审视的目光。第二,
帮助的“有效期”社会帮助往往有“有效期”。当一个人长期处于困境,
周围的援助会逐渐减少,最后消失。“开头几年,还有老同事来看看我,
后来大家都忙自己的生活,就慢慢不联系了。”老陈平静地说,“我能理解,
谁有那么多精力总顾着一个掉队的人呢?”第三,
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”的陷阱当老陈一次次尝试工作失败后,
有人开始认为他“不努力”、“不上进”。甚至有人说他活该,因为他“不懂变通”,
不会在新时代里寻找机会。这种指责忽略了一个事实: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迅速转变的能力,
特别是对于一个在计划经济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中年人。第四,
系统性援助的缺失当年的下岗潮席卷了整个社会,像老陈这样的人成千上万。
有限的社会资源无法为每个人提供真正有效的、个性化的帮助。
大多数援助停留在基本生活保障层面,无法解决精神创伤和技能落后等根本问题。
6 最后的告别最后的尊严在我认识老陈的第三年春天,他病倒了。
那天我发现他两天没出门,敲门无人应答,便找来房东开门。老陈躺在床上,发着高烧,
身边是几个空矿泉水瓶和半袋馒头。我们送他去医院,诊断为肺炎。
医药费是我和几个邻居凑的,他得知后,不停地道歉:“对不起,给大家添麻烦了。
”住院期间,老陈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。他甚至和我们开玩笑,说等出院了,
要请我们吃饭感谢我们。但一周后的凌晨,护士查房时发现他已经安静地走了。没有痛苦,
没有告别。整理遗物时,我们发现他的铁皮盒子底层,除了那些旧照片,还有一张存折,
里面有三千多块钱。还有一张纸条,
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:“这些钱应该够火化和墓地的最低费用。不想再麻烦任何人。谢谢。
”7 时代的反思反思老陈的故事,是一个被时代碾过的人的悲剧。他并非不努力,
并非没有才能,只是在社会转型的巨轮下,他成了被牺牲的那一个。而我们这些旁观者,
常常陷入一种自以为是的帮助误区:我们提供我们认为对方需要的东西,
却很少真正倾听他们内心的需求;我们期待被帮助者立刻振作起来,
否则就会失去耐心;我们习惯于用“可怜”或“可恨”来简单定义一个人,
而不愿理解他们所处的复杂境遇。老陈去世后,我常常想起他的一句话:“我不怨天不怨地,
只怨自己没本事跟上这个时代。”但真的是这样吗?当一个社会飞速前进时,
是否也应该回头看看那些被落下的人?我们是否能建立更有温度、更持久的援助机制,
不仅解决生存问题,更能修复受伤的尊严?老陈的悲剧不在于他贫穷,不在于他孤独地死去,
而在于他曾是这个社会建设的一部分,却在社会前进的过程中被无情地抛下了。
而我们每个人,都有可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“老陈”——在生活的某个转角,
被命运的重拳击倒在地,需要一只援手,需要一点理解,需要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机会。
帮助一个跌倒的人,需要的不仅是短暂的怜悯,
更是持久的关怀、尊重的态度和对复杂性的理解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老陈的墓碑很简单,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。但每次去看他,
我都会想起他常说的那句话:“人啊,活得要有尊严。”8 遗物中的秘密也许,
真正的帮助,就是让每个人在困境中依然能保有尊严。老陈是在周五凌晨四点半被发现的。
打扫楼道的清洁工闻到异味,敲了半天门没反应,找来房东开门,才发现他身体已经凉了。
警察来了又走,排除了他杀,说是突发脑溢血。房东在老陈那铁皮盒子里翻找一通,
找到一张纸条,上面工工整整写着我的电话号码和一句话:“如遇不测,请联系此人,
费用盒底存折。”我接到电话时正在赶一份设计稿,听到消息,鼠标从手中滑落,
在木地板上磕出一道白痕。老陈的遗体被送到了殡仪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