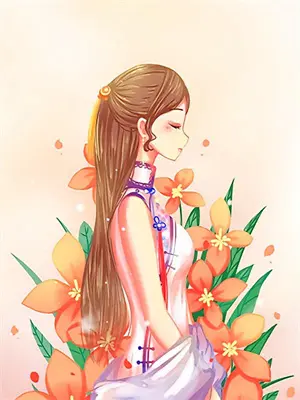
我是秦宫,大将军梁冀的男宠。他亲手将我养大,教我权谋,让我成为他最锋利的刀。那天,
他夫人孙寿将我唤入闺房,指尖划过我的衣襟: “你这样的美人,不该只属于将军。
”我垂首不语,袖中匕首冰凉。梁冀在门外阴影处微笑观望,
而我知道—— 他教我的第一课,就是如何让女人心甘情愿地赴死。1我是秦宫。
他们都这么叫我。宫,宫室的宫。我知道这名字背后的轻蔑与暧昧。
我是大将军梁冀的“宫”,是他华美牢笼里最珍奇的一只雀鸟。梁冀,当朝大将军,
权倾朝野,连天子也要让他三分。他身形高大,年轻时想必是极英武的,
如今岁月和权势在他身上沉淀出一种深沉的威压,不怒自威。他看人的时候,
眼神像是能剥开皮囊,直刺灵魂深处。是他把我从那个肮脏破败的街角带回来的。
那年我大概八九岁,缩在墙角,看着他那双织锦的靴子停在我面前,碾过污水,却纤尘不染。
他抬起我的下巴,指尖粗粝,带着常年握剑留下的茧。他端详我的脸,像是在鉴赏一块璞玉。
“根骨不错,眼神也干净,”他当时这么说,语气平淡,听不出喜怒,“带回去,洗刷干净。
”那是我命运的转折。从泥泞到云端,只在他一念之间。他亲自教我识字断文,
教我权谋机变,甚至请了师傅教我剑术。他把我带在身边,出入府邸,
有时甚至允许我旁听一些不那么紧要的议事。他抚着我的头顶,对幕僚们说:“这孩子聪慧,
是一把好刀,要好生打磨。”我是他的刀,也是他的宠物。夜晚,
在那间充斥着檀香和书卷气息的房间里,烛火摇曳,
他粗糙的手指会缓慢地抚过我光洁的脊背,声音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慵懒:“秦宫,
你要记住,是谁给了你这一切。你的命,你的魂,都是我的。”我伏在柔软的锦褥中,
脸埋藏在阴影里,轻声应答:“是,将军。”我确实是他的刀。
一些他不便亲自出手的“麻烦”,会由我去了结。有时是用袖中短剑,有时是用他教的计谋。
他教会我的第一课,并非杀人技,而是诛心术。那年我十一岁,
他领我到后院那口废弃的古井边。井沿爬满青苔,幽深不见底。一个侍女跪在那里,
衣衫凌乱,面无人色,浑身抖得像风中的落叶。他递给我一把装饰华丽的匕首,
冰凉的刀柄塞进我汗湿的手心。“她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,”梁冀的声音平静无波,
像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小事,“去,让她自己跳下去。”我的手抖得厉害,匕首几乎脱手。
那侍女抬起头,泪眼婆娑地望着我,眼神里是纯粹的、动物般的恐惧。“告诉她,
”梁冀在我身后指导,语气不容置疑,“若她心甘情愿跳下去,她的家人可得百金,
安稳度日。若你动手,或是她发出半点不该有的声音,便是满门抄斩,鸡犬不留。
”我强迫自己走向前,双腿如同灌了铅。我重复着他的话,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。
那侍女听完,奇异地停止了颤抖。她用一种近乎空洞的眼神看了看我,又越过我,
看了看阴影中的梁冀。然后,她俯下身,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。站起身,没有丝毫犹豫,
甚至带着一种决绝的平静,纵身跃入了井中。“噗通——”那声闷响在我耳边回荡了许多年。
梁冀走过来,拿回匕首,用雪白的绢帕擦拭着刀柄上我留下的汗渍。
他的手按在我僵硬的肩膀上。“看明白了么,秦宫?”他的声音里竟有一丝奇异的满意,
“杀人,最低等的是亲自动手。高明的,是让她们自己走向毁灭。尤其是女人,
她们往往比男人更懂得权衡,什么叫‘心甘情愿’。”我胃里翻江倒海,冷汗浸透了内衫。
那口井的幽深黑暗,和那侍女最后空洞的眼神,成了我许多个夜晚的梦魇。我渐渐长大,
容貌愈发符合梁冀的喜好,清俊中带着一丝不易折损的韧性。他待我愈发不同,
赏赐流水般下来,绫罗绸缎,古玩珍奇,甚至允许我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。府中上下,
无人敢怠慢我,即便背过身去,那些目光里混杂着嫉妒、鄙夷和畏惧。我知道自己的位置。
我是梁冀的私有物,是他权力和欲望的延伸。我谨慎地扮演着我的角色,收敛锋芒,
温顺驯良,将那个在噩梦中惊醒的少年死死压在心底最深处。2直到孙寿的出现。
孙寿是梁冀的夫人,一个美得极具攻击性的女人。她的眉鬓描画得斜飞入鬓,看似慵懒蓬松,
却暗藏锋芒,那是时下京城贵妇竞相模仿的“愁眉啼妆”,据说就源自她的巧思。
她走起路来摇曳生姿,仿佛弱不禁风,可那双眼睛,看人时却像带着钩子,
能轻易剜下一块肉来。她第一次正眼看我,是在一场家宴上。梁冀让我在一旁侍奉笔墨。
孙寿斜倚在软榻上,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过我,停留了片刻。那目光不似旁人带着明确的情绪,
而是一种纯粹的、打量物件的审视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味。后来,她开始偶尔召我。
虽然她自有眼线;有时是让我辨认一些古玩上的铭文——我确实被梁冀逼着学过这些;有时,
似乎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理由。每一次踏入她所居的“蕙香阁”,
都像踏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与梁冀书房那种沉肃、充满权力感的氛围不同,
这里极尽奢华香艳。南海的鲛绡帐,西域的琉璃屏,
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种复杂而甜腻的暖香,闻久了让人头脑昏沉。
地板上铺着厚厚的西域绒毯,踩上去悄无声息,仿佛一切声响都会被这柔软的深渊吞噬。
她常常穿着宽松的寝衣,云鬓微松,赤着脚,在铺满地面的锦绣堆里走来走去。
她会跟我说话,内容天马行空,从宫闱秘闻到市井流言,有时甚至会带着几分戏谑,
点评梁冀的某些政敌。“那个李固,仗着是清流领袖,总跟大将军过不去,
”她捻着一颗冰湃的葡萄,指尖染着鲜红的蔻丹,像血滴,“听说他夫人前日病了,
病的真是时候,你说是不是?”我垂首站着,不敢接话。她便会笑起来,声音像玉珠滚盘,
清脆却冰凉:“怕什么?这里只有你我。大将军既然允你过来,便是信你懂得分寸。
”她的话像蛛丝,一层层缠绕上来,看似轻柔,却带着黏稠的束缚感。我始终保持着沉默,
或者用最谨慎、最无关痛痒的话应答。袖中那柄梁冀所赐的匕首,
时刻提醒着我自己的处境和危险。3我一一禀报,不敢有丝毫隐瞒和添减。他听着,
脸上是那种惯有的、高深莫测的表情,有时会点点头,有时只是挥挥手让我退下。
我看不透他的想法。他是默许这种试探,还是乐见其成,将这也视为对我的一种磨练?或者,
他只是在等待,等待我露出丝毫动摇的迹象?这种微妙的平衡,在一个闷热的午后被打破了。
那日,蕙香阁里的熏香似乎格外浓重。孙寿遣退了所有侍女,只留我一人。
她斜靠在窗边的贵妃榻上,望着窗外一株开得正盛的石榴花,火红的花瓣映着她雪白的肌肤,
有种惊心动魄的美。她许久没有说话,阁内静得只能听到彼此轻微的呼吸声,
以及我袖中匕首贴着手臂的冰冷触感。“秦宫。”她终于开口,声音带着一种慵懒的沙哑,
像羽毛搔过心尖。“夫人在。”我微微躬身。她缓缓坐起身,赤足踩在柔软的绒毯上,
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那袭轻若无物的鲛绡长裙曳地,随着她的走动,像一团流动的霞雾。
她走近我,停在我面前,很近,近得我能感受到她身上散发出的温热,以及那温热之下,
一丝属于名贵香料的冷意。她的指尖,染着那抹刺眼的红,冰凉如同初春解冻的溪水,
轻轻点在了我的下颌。然后,缓缓向下,划过我的喉结,沿着官袍严谨的衣襟边缘,
一路游走,带着一种审视器物的挑剔,和一种毫不掩饰的、隐秘的贪婪。我的呼吸一滞,
浑身的肌肉在官袍下绷紧,像一张拉满的弓。袖中的匕首,
那冰冷的金属触感透过薄薄的里衣,刺醒着我的神智。
“真是一副好皮囊……”她叹息般低语,气息带着暖香,拂过我的耳廓,“他倒是会挑人,
也舍得下本钱养你。”她的指尖停在了我的胸口,感受着其下骤然加快,
又被我强行压制下去的心跳。4“秦宫……”她唤我的名字,舌尖仿佛含着蜜,
“你这样的美人,聪慧,隐忍,懂得审时度势,就像那淬了毒的翡翠,漂亮,又能致命。











